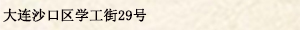萌芽经典绝味
编者按
平凡的生活就像熄了火的砂锅粥,断了电的热水器。不过总有那么几个爆发的时刻,想要奋力一跃,试图冲破这毫无意义的、日复一日的存在……这样就能破涕为笑吗?
作者吴晶晶
地铁行到南礼士路的时候,自动门旁的小电视机上正在教如何做红茶排骨。
克排骨焯水洗净,锅内上油,姜片爆香,同时加入酱油和沥干的排骨,翻炒上色,重新加入水、香料,等到锅内煮物再次沸腾时,放入茶叶包,炖至软烂。
“南礼士路到了。”广播里播报说,然而她已经来不及继续往下听了——手心上密密麻麻地传来震动感。她胸有成竹地滑动锁屏,果然是胖子的信息。
17:09
胖子:
那今天也很辛苦吧,小孩本来就又是天使又是魔鬼啊。
晚上吃点好的吧,犒劳自己。[太阳]
她脸上燃起笑意,随着上下车的人流,往自动门边换了换。她一面倚在栏杆上回信息,一面在心里暗自用余光打量:车上这些人里,一定有一两个注意到我正在一面笑一面打字吧?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是不是在猜测,这大概是个正在恋爱时期的女人?
反正她自己是这样的,独自乘车的时候,如果手头没有事干,总是在默默观察别人,别人的表情,别人的衣服,别人的手机屏幕,聆听别人打的电话,一搭一唱地聊的天,万一刚好人多拥挤,兴许还能瞟到对方的聊天内容。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甚至还想做个调查,调查在一万个和她一样看上去普普通通、一板一眼的人当中,有多少个也会情不自禁地被陌生人的世界所吸引。关于这一点她还从没对阿武说过,但她告诉过胖子。胖子说他一般还是自顾自玩手机的时候居多,但要是晚高峰时别人的手机被挤到眼皮子底下,会忍不住想看一眼,大概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毕竟人类是靠好奇心才发的家。
有一次地铁上两个人吵了起来。胖子说,因为一个人用手机看报纸,另一个人就跟在他后面一起看,被偷看的人发现了之后觉得很不自在,特地调整了姿势,结果偷看的人也顺势跟了过来,想继续白看。于是两个人就立即吵了起来。
其实一块看也没什么吧,反正那个人也没说话。陈木樨说。
但你想想,如果你跟我说的这句话正好被别人一字不漏地偷看了,你会怎么想。胖子反问。
那不一样。她回复道。报纸本来就是给全世界看的,但我发给你的信息——屏幕上光标在这里停了一下,在那空白的几秒钟里,独自一闪一闪地跳跃,然而它很快又再次恢复运作——是只想给你一个人看的,这和报纸当然有本质区别。[发送]
“木樨地到了,请——”
广播里话还没说完,她倒是吓了一跳,赶紧蹿下车去。回一条信息竟然这么出神,万一坐过了站那可就笑话了。
然而谁又会笑话呢?世界上谁会知道谁会在意陈木樨在某个夏天星期一的下班时间坐过了站,整整多坐了几站才想起来下车呢?阿武不会知道的,胖子也不知道,除非她告诉他们。然而即使她对他们说了,也不过是想获得安慰,想借此展示自己“迷糊笨拙”的一面。毕竟如果有女孩说自己因为太累了或者专心回复他的消息而忘记下车,男生多半会觉得她很可爱吧?
她这么想着,一边往出站口走,一边再次摸出手机。
17:13
木樨:
不知道吃什么好。
刚才因为回你的信息,竟然忘记下车了!![发呆]
她混在匆匆忙忙的下班人群里出了闸口,路过ATM机、临时证件照自助拍照机和价格比外面贵了一半的自动贩售机,踏上自动扶梯,再和几个赶去搭车的人一上一下地擦肩而过,她便再次成功地回到地面了。回身一望,蓝底白字的“木樨地地铁站”正横在眼前。
当初找房子时她想都没想就决定必须住在木樨地这里。可能是名字的缘故,她刚调到北京来时一下子就被这个同名的地铁站吸引了,觉得有种宿命般的归属感。虽然房费远远超出预期,但她还是坚持无论如何得住在这里。后来她问父亲,取名字是不是因为这个。然而对方说,以前的确是来过北京,但不记得有这个地名,甚至连那时候有没有坐过地铁都不记得了。她之所以叫陈木樨而不叫陈木桩或是陈蜥蜴,完全是因为当时翻字典,第一个翻到的是mu,第二个翻到的是xi。因为觉得木字踏实,所以就选了这两个字。
但她也丝毫不觉得失望,反正都是给自己一个花钱的借口而已。毕竟普普通通的人,哪配谈什么宿命。
而实际上木樨地却和她本身一样普通。
被手机贴膜霸占的天桥,路边每天一争高下的枣糕和南瓜蜂蜜蛋糕,各种各样不大不小的饭店,违规过马路的行人,车站附近的水果摊子,总比巷子里的一斤贵两块,这是木樨地;没有像样的商场,没有像样的写字楼,周末闲下来往往也是觉得没有什么像样的值得一去的地方,要看电影买衣服就得坐公车去西单,这是木樨地;当人们说去逛街,人们说去西直门吧去国贸,当人们说吃饭,人们说去三里屯吧去五道口,当人们说观光,他们说去鼓楼吧去后海。然而人们什么时候会说到木樨地呢?这明明也挂在古老辉煌、名声赫赫的一号线上,看上去最清新淡雅、独树一帜的一笔。
陈木樨能想到的结果,仅仅是有一次阿武在外面吃饭,喝多了,她接到熟人的电话就赶紧去饭店接人,回来时实在没办法,破天荒地打了车,师傅从前排侧过脸来问她去哪,她一面忙着把烂醉如泥的男友扶正,一面头也不抬地答道:“去木樨地。”
这就是木樨地了。
不知道是木樨地的普通感染了她,还是她与生俱来的平庸加重了木樨地的晦暗,无论是早上一面拿着包子一面匆匆前往车站的路上,还是自己带着购物袋去小超市买菜的傍晚,陈木樨常常觉得自己已经和那些风尘仆仆的、充满市井意味的街景融合在一起,仿佛她是一棵树,一根电线杆,一个无人问津的邮筒,如果不是结账拿零钱时硬币蹦出来,一路顺着地砖溜进角落,恐怕就没人能够发现她。
她就是这样透明的人,不论在学校还是在木樨地,她似乎无时无刻不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多一分也无味,少一分也不觉得可惜,只要她愿意,她就能像只透明的蜘蛛网一样活着。从木樨地车站出来的十几分钟后,当她一如往常地穿着隐形的外衣走进小区,单肩包里又震动了一下,打开拉链的时候,她脸上又浮出那种模模糊糊的笑意。
17:29
阿武:
饿了,买饭回来吧。
他们现在住的是五层式的老房子,楼道里终年累月弥漫着一股霉菌孢子的味儿,前几年总有人家在拐角上放腌酱菜的大缸,后来因为城市文明建设的问题就被勒令禁止了。然而这栋房子的气血不是挪开一口酱缸就能拯救得了的,一圈圈的扶手上照旧生了锈,青一块紫一块的白墙上仍然粘满了通下水管和开锁公司的小广告。有时陈木樨甚至觉得那些小广告根本不是由什么人贴上去的,而是这栋楼本身生长出来的东西,今天在这边除掉了,明天又会在那边长出来一点。原来他们家门口的福字上被人贴了一块广告她都气得不得了,每天晚上都拿小剪子在那里刮,然而到后来累了,疲乏了,习惯了,也就放弃了,听之任之,眼下红色的福字早已被埋没得无影无踪了,她也绝不会去管它,每天开门关门都视若无睹,像曾经爱过又后来放手的旧情人。
一进家门,她首先踢掉高跟鞋,然后一边用脚脱丝袜一边手伸到背后去解连衣裙的拉链,接着是耳环,镶着假钻石的头绳,最后是成套的淡粉色内衣裤。
租来的房子本来是没有淋浴的,因为卫生间本来就很窄,几年前刚住进来的时候她一直都是拿着洗具去大众浴池,只是后来又多了一个人,当时的她舍不得也让对方走上20分钟才能洗澡,一到冬天从澡堂子回到家,头发上全是小冰碴。而且另一方面,离家最近的浴池那会儿也挂上出兑的牌子了,平价的洗浴中心早就遍地开花,这种老式的大众浴池撑到现在已经全是靠着老顾客的情面,总有一天要花光的。
然而房东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因为还涉及到重铺防水地砖的问题,她来来回回跑了一个月,才最终决定为,她出钱买热水器,房主出钱搞装修,退租以后热水器给他留下。虽然有点不甘心,但总算是不用忍受在女澡堂子里,几个全身赤条条的大中小女人互相用余光斜斜打量的痛苦了。
热水器就安在马桶上方的墙壁上,她光脚踩在地砖上,猫下腰把碎花图案的马桶垫拆下来,并顺手把盖子上的卫生抽纸拿走放到一边,以免被水淋湿。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五点半多了,一会吃过饭收拾完毕之后就是七点,然后要看开会的文稿准备上课的课件,怎么也得三四个小时。陈木樨心里一面盘算着,一面在花洒下闭紧眼睛冲头。
“唉,你没买饭啊?”这时厕所的门被“晃啷啷”拉开了,蒸汽消散的尽头站着她故事的男主人公。
“干吗啊你,”她一把把拉门关上了,“水溅出去楼下又要来闹了。”因为之前有一次阿武洗澡时没关门,水流到外面的木质地板上渗到了楼下去,最后赔了一千块钱。
“我不是给你发信息了吗,你没看见吗?”一片水声里他的声音离开了一点,应该是去冰箱里找吃的去了。
“我进门之后才看的手机。”她再次把眼睛紧紧闭起来,往头发上抹香波。
“我真是服了你了,”隔着流水的噪音,潮湿的鼓膜上隐隐约约地接收着阿武的声音,“那一会你做饭吧,炒饭就行了,我看冰箱里还有点肉啊菜啊的,我都要饿死了——”
“叫外卖吧,等我做好了都能看新闻联播了,而且我今天特别累。”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洗头,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演,明明他现在也没有在看自己的。
玻璃门外顿了顿。她能想象出阿武生气的神色,门里门外,只有泡沫顺着皮肤簌簌滚落的声音。
“你吃什么?”男友问道。
“你说什么?”有一团泡沫刚好把耳朵堵住了。
“你吃什么?”
“随便点吧,看你想要什么,我不太饿,但人均不能超过二十五块钱啊。”
“反正吃来吃去就是那几样东西,有什么好选的。”门外的影子说,那之后他好像又问了个什么问题,她还是没听清,但已经不想再追问了,因为心里知道,也不过就是吃吃喝喝那点事。
身体对面就是洗手台的镜子,镜前的架子上杂乱无章地站着洗发香波、沐浴液、阿武的磨砂洗面奶和她的泡沫洁面乳、卸妆水,以及各种各样已经叫不上名字的瓶瓶罐罐。于是镜子映出来的影子,也就只剩下乳房以上的部分。她把水雾拨开,看见对面一张妆容全无的脸。上大学的时候她一直是素颜主义者来着,但实际上也没什么主义不主义的,她心里知道,无非是懒而已,而且看上去漂不漂亮,那时也不能带给她什么满足感。和阿武谈恋爱之后——那时已经上班了,有一次公司聚餐,那一阵同事还都未得知两人的关系,席间他们讨论起女孩化妆的问题,喜不喜欢化妆,浓妆好还是淡妆好,其实只是无聊的美容话题,倒是引起了人群之间的大讨论。等问到阿武头上,他说,淡妆就行了,但化妆是必不可少的吧,多少还是要有一点。感觉是对其他人的尊重,一起工作的人也好,一起吃饭的人也好。他当时笑着说着,面前是他爱吃的盐烤银杏,右手边上是喝了三分之一的冰啤酒,放大了看,似乎还能看到濒临死亡的气泡仍然在表面无望地挣扎。
他的视线并没有一刻落向她,那时垂爱她的唯有头上灼热照射的灯光。她似乎能感到自己脑袋中间变成一只放大镜,不断地吸收着光线、笑声、铁板烧上冒出来的蒸汽,并最终将之转化为熊熊的热度。就快要把她烧着了。
她想她是从那顿饭开始醒悟了。每天必然花上一个钟点在微博上做功课,从试用装到正品装,从粉饼到眼影——她本来没有想要这么贪婪的,然而当费尽功夫擦了脸,就想着还是画上眉毛和眼线吧,待到后来熟练了,总觉得脸色惨白,就问自己应该还是要擦个腮红吧。然而等到腮红都有了,眼影就显得更不可或缺了。于是每天上班时眼睛里总在暗暗观察,给每个人打分,这才发现,原来素颜派除了她以外就寥寥无几,只不过是过去自己全不在意罢了。有时她洗手时照镜子,简直不能想象过去蓬头垢面的日子。关于这样的心理变化她从未向阿武提过,只是她会在心里暗自雀跃,假如即使是那样子阿武也能爱她,那想必一定是因为她的其他的美。
而那其他的美到底是什么呢?她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她本来就不是那种会拿这样的问答缠人的类型,况且,她也早就不在意答案了。
“想什么呢你,”拉门猛地被人拽开了,门外是那日的灯光下曾令她灼热难当的人,“吃黄焖鸡行吗?”
“关上关上,干吗啊你!”她赶紧关了水拉上门。
“我问你好几次了你都像聋了似的。”他吃着紫色嚼益嚼,也生气地说。
“水声太大我没听见啊,你大点声不就完了。”她几乎是冲着镜子翻了个白眼。因为刚才关了水觉得身上有点发冷,这让她更觉得有些烦躁。
“你吃不吃?”在再次响起来的淋浴声中,他说。
“你看着办吧,我什么都行。”她答道。
对,就是因为这样。镜子里的裸女说,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不在乎的,不在乎他是爱我什么,不在乎他觉得我美不美。就算曾经觉得又能怎么样呢?你看现在,迟早都会消退的,曾经觉得新奇的、为之深深吸引的东西,等看清了之后就发现也不过如此,到头来也还是要每天为了是吃鸡还是吃牛吵,为了是黄焖鸡还是盐焗鸡吵。
阿武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么不可爱了。面对裸女灼灼的质问,她的视线有些躲闪了,眼珠子转到右边,落在刚被自己拆下坐垫的光秃秃的马桶上。那一瞬间她回忆起许许多多事情,她想起小时候曾经一度觉得马桶很神圣,因为想到,不论多有名的人,总是要上厕所的,而一上起厕所来,大概全天底下的人都是一样的丑陋,面部狰狞。想起上中学时学校组织旅游,因为在休息站睡着了错过了下车时间,之后足足在大巴上忍了两个钟头的事。而在那林林总总的回忆中间,自然少不了那天的洗手间,那个夜晚的马桶。她看见那时的自己站在一平方米的空间里,手已经扶上了腰间准备解扣子,心里却有些迟疑。
那是几年前的同一个夏天,一样的令人皮肤发黏的热度,一样的迟迟不落的夕阳,是为了什么原因她已经不记得了,只是那一个星期她每天都必须留下来加班,当然不只她一个人,除了她们编辑部门的几个同事,还有网络工程的两三位技术员。几天加班下来,一起等电梯,或是在休息室碰见了,来来回回出现的就是那么几张脸孔,本来不熟悉的人之间也不得不看了个脸熟。然而那天是星期五,旁的人都尽快早早赶工出去度周末了,她因为那一会感冒了,又是刚从小地方上调过来没多久的新员工,本来进度上就有点拖沓了,等到了周五,更是全都压了下来,所以等到了九点多,一百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就只剩下她和一个技术员。她自然是知道对方的名字,但因为从来也没说过话,现在无端开口也就更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整个空间里只有两个人各自打字的声音,空调机制冷的风声和他一下一下扣响鼠标的咔嗒声。
中途陈木樨起身去上厕所,她起立的时候也尽可能地小心,轻轻地把椅子抬起来再放下,因为她总觉得有点害怕引起对方的注意,好像一点点噪音都能破坏这秘而不宣的和谐。然而等她走到洗手间,却发现灯黑着,摸出手机找开关,上上下下按了十几次,却仍旧一点反应也没有。她想着,要不就这么进去吧,但最终还是胆怯了,因为觉得恐怖。光是想想一个女人开着手电筒坐在马桶上,就感到寒意从背后不请自来了。
“灯坏了吗?”蓦地,身后有个声音说。
陈木樨结结实实地尖叫了一声,那个人好像也着实吓了一跳,因为在黑暗中能感觉到对方往后弹开了一步。
“好像真的是坏了。但下班时还有人用来着吧。”她说着,又象征性地按了两下开关,像是要证明自己说的话似的。
对方沉默了片刻,在那寂静的十几秒里陈木樨脑子里闪过了好几种剧本,既然是玩电脑的,可能电器类的也在行?还是他会说,这楼里其实另外有总的控制开关?或是本来每天过了九点以后,大楼里的一部分区域就会自动断电,好为了节约能源?
然而还没等她的颅内小剧场设计完毕,他的戏就已经开演了。
“这样吧,你进去,我在外面等你。”他说。
她电话上的手电筒还依旧亮着,亮光不知道该对焦在哪里。微弱的光线把他下颌骨左侧的痣映得一览无余,T恤衫反射出一点点星星似的亮光。
“你要是害怕的话我就玩会儿游戏,音乐一直开着。”黑暗里的人影把手机举起来晃了一晃,再次向她确认道。
站在一平方米的隔间里,面对着马桶里粼粼的波纹,陈木樨手放在腰间,觉得膀胱就要爆炸了,而裙子却迟迟脱不下去。她脑袋里反反复复地想着,这里这么静离得又这么近,恐怕小便的声音也会被听个清清楚楚吧?然而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什么也不做就出去了岂不是显得更奇怪?小单间里的空气眼看着要爆炸了,然而几米之外走廊上的气氛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格外有节奏感的战斗音乐一刻不停地传来,吵闹得要把整栋大厦都惊醒了。
像是受到了那曲调的鼓舞,她心一横,屁股一沉,“扑通”坐了上去。
那是她人生里最长的一次小便,陈木樨想。明明短短的几十秒,时间感却因为紧张而成倍地增长。那种度日如年的心情她觉得自己常常有,一直以来就是。不论是上学时,在讨厌的课上等下课的时候,自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时钟,每过五分钟就把分针擦掉,重新前进一格;还是许多年后在公司面试上等着叫到自己名字时,明明也不过二十几分钟而已,站起来的时候裙子却已经因为出汗牢牢地粘在大腿上了。
现在她偶尔会怀念起那时的心情,那样的燥热,那样的心急如焚。因为现在完全是吃了退烧药的生活,熄了火的砂锅粥,断了电的热水器。他们之间平凡的爱情被平凡的人生充斥着,而那平凡的人生也无外乎是由一顿顿平常的饭菜构成的。在莲蓬头下仰起脸,回忆生活里的细节,她发现自己许多事情都忘记了,就唯有对吃饭这件事记忆非常清晰:今天早上吃的是好利来的丹麦红豆面包,她给自己用微波炉热了一杯牛奶,阿武起得晚,吃的是她剩下的另外一半。昨天晚上吃的是人均十五块钱的凉皮外卖,前天早晨吃的还是面包。大前天早上是星期日,两个人都是过了中午才起来,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叫了外卖,傍晚的时候,一起走到电影院去看了场电影,用团购软件买的票,出来之后觉得肚子饿了,在回来的路上买了一份加了香肠的烤冷面和都可奶茶。为了多喝一点奶,阿武还特地要了不加冰的。
那一路上他们说过什么话吗?她对于电影说了点什么吗?阿武呢,他说了点什么吗?
她想起来的只有模模糊糊的空白,就好像每天洗澡时热水不仅带去了头发上的泡沫和污垢,而且连大脑皮层里名为“记忆”的汁液也一并冲走了。
从浴室出来的时候阿武还在打游戏,她裹着浴巾去卧室里找换洗内衣。她一向对于这方面很是上心,哪怕一个月里不添置一件新衣服,但内衣裤总是要定期买的,而且她通常都成套成套地购买,或是买相近的颜色自己回来搭配,有蕾丝花边的,镂空设计的,有绣花图案的,不一而足。为此她时常觉得自己的内在远比外在要来得精彩得多。她不知道阿武有没有曾经注意过这些细枝末节,因为他从来没说过,于是她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做了有什么意义。但她这次还是按部就班地换上新的藕荷色刺绣花边内裤,同色系的乳罩放在床头柜上,预备明天穿。尽管她心里很清楚这些美丽都是无望的,无望得如同她自己本身。
完成自己煞有介事的仪式后,她重新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一边擦头发一边检查手机。
17:37
胖子:
[发呆][发呆]
[偷笑][偷笑]
18:15
胖子:
所以你还是没说晚上吃什么了?吃饭了吗?
她正要开始打字的时候,余光瞥见男友也拿起了电话。他右手操纵着鼠标,左手迅速地解锁,点开未读信息。陈木樨从沙发上弹起来,假装去厨房倒水。从电脑旁边经过的时候,她迅速把脖子一低,看了一眼他的手机屏幕。——具体内容倒是次要的,光是靠着黄色的辛普森头像她心里就有数了。那是他们以前公司里的同事,过去倒还不觉着,阿武辞职后几次跳槽,到现在在家待业,在这段颠沛的时期里对方却反而主动了起来,仿佛是因为距离产生美了似的。陈木樨从来没有当面问过男友,但她心里都明镜儿似的。对方明明知道她和阿武的关系,也自然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辞职的,这一来一往还做得这么明显,她可不信什么“好朋友之间的友谊”那种堂而皇之的解释。每每想到这里她都有点生闷气的意思,她既生气辛普森那样的女人,以为自己顶着天真的头像打着好哥们的名义就能演得了无故好人了吗?同时她也生阿武的气,露出失意男人寂寞的皮相,无形之中也抹杀了她的自尊。
他们之间已经进行到哪步了,陈木樨没有明确的证据,她所能获得信息的渠道,就是阿武洗澡时手机锁屏上的信息预览和那位女性的微博——她每天发了什么照片做了什么事情,谁发了什么评论,陈木樨每天都能看个好几遍,由于查看得过于频繁,为了避免自己手滑点赞,她还让自己养成了个左手看微博的习惯。尽管阿武从来没有在社交网络上和她互动过——不知道是因为的确有猫腻才不得不避嫌,还是因为真的是还没有深交到那个地步——但总而言之,这个让她觉得自己十分卑小的习惯,她至今都没改过来。每天洗完澡后吹头发的时候,每天吃过饭把碗泡在水池里等待清洗的时候,每天早上在安检之后等待一号线姗姗来临的那几分钟几百秒,她常常都是熟稔地通过以前同事的北京白癜风的有效治疗方法脚上白癜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