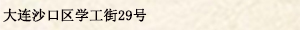李静睿代表作感受她的冷漠
卖毛线的女人
电影院是小城最后暗下来的一盏灯。它总是断断续续地开张,随后又漫长地关闭,每一次重新回来,都毫无征兆天声息,大门外的劣质海报多少年来都没有换过,成龙或者周润发身上落满灰尘,有人用红色圆珠笔在海报上写着“林美美我爱你”,后面有一支箭穿过至至扭扭、没有填满的红心。售票窗是一个小小的铁栅栏,一个头发烫得很乱的中年妇女终日坐在后面,永远拿着两根细细的银色钢棒打毛线,有买票才停下来,潦草地撕一张递出去。小城的电影院从来不场次,用五块钱买上一张票,可以在破破烂烂的红色椅子上上一天,地上瓜子売慢慢变成厚厚一层,走时像踩在沙沙的叶上,屏幕后面隐约飘来饭菜香,放映员在吃蒜薹肉丝蒜苗刚绿,又换成蒜苗回锅肉,冬天用胡萝卜烧鸡,隔着屏幕也觉得胡萝ト很甜。又经过售票窗,中年妇女已经下班了、只有那堆毛线搁在里面,像某种动物安静下来,有时候是暗红色打平针,穿在里面打底,偶尔会有天蓝色,大概是打给女儿的上下针又打成花瓣领,胸前一只黄色小鸭子。
我从来没有看清楚过卖票女人的险,也许这么多年,早就换了人,也许她们都一样烫着满头乱发,大概是在电影院旁边的同一家发廊做的,最开始只要十五,后来变成三十,头上套着一个个的卷发器,坐在硕大发热的机器下面,头发被烫得焦黄,是冬天里晒干的麦秸,梳头时有脆脆的声音。
生意清淡时,卖毛线的女人也去发廊坐坐,毛线针上下翻飞,打手套或者围巾,和做头发的女人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露手指的手套专门卖给学生,做作业也不用取下,两块五一双卖一双她能挣一块钱,她打得飞快,琢磨了各种花色,有时候垂下几个毛线球,有时候在手心里开出几朵花,有时候是一朵蓝色的云飘在手背上,颜色嫩黄翠绿粉红,又怕大人们替孩子买,所以也打了几双耐脏的褐色藏蓝,老老实实上下针,没有做花。
她女儿戴着一双这样的藏蓝色手套,用的是纯羊毛,这种毛线价格很高,买的人不多,她刚开始卖毛线的时候进了一批货,几年都没有卖光,每年夏天都得在大太阳下摊开来晒一次、晒了几年微微有点褪色,更不容易卖出去。小城的女入们都买三七毛,穿起来结实,只是有一股腈纶的怪味。
女儿中午放学来她的摊上吃饭,大部分时候吃早上准备好的饭盒,在隔壁小炒店的蒸笼里热了,昨晚炒的青根肉丝已经又黄又软,烧的鲫鱼只剩下几个乱糟糟的鱼头,还好有早上新抓起来的泡豇豆,拌着麻油海椒,一饭盒米饭很容易下去。有时候上午生意好,她们就在小炒店里吃,小煎鸡三块钱一份,没几块鸡肉,又都是脖子和鸡爪,一般都是女儿吃了,只有偶尔遇到鸡屁股,女儿就细心地夹给她,鸡屁股的肉嫩,但吃不惯的人觉得有一股臊气。
等到女儿下午放学,趴在推前的小凳子上做完作业,她们就收抬着把毛线锁在电影院仓库里,每年都要偷偷给守门的人买几条烟,过年又拎上香肠腊肉去拜年,他才别别扭扭答应,又早早声明好:什么责任都不负,被偷了就算她倒霉。她买菜时挑栋许久,女儿就在路边等她,拿出一本英语教材大声背单词,英语老师从来没有出过国,她的口语也有明显方言味,来来往往的熟人都说,这个幺妹好乖。
地们拎着一根莴笋一点泥鳅回家去,似乎已经闻到莴笋烧泥鳅中小米辣椒的味道。沿途黑沉沉的,路灯渐次亮起来,但无论何时,电影院总是小城里最后暗下来的一盏灯。
她女儿是我同学,从小学开始就是同学,我们都坐第一排她和我隔着一个位置,不管什么时候我扭头过去,都能看到她憋红了脸正在做作业。
她叫张慧,班里还有一个女孩叫张卉,张慧什么都要大,所以是“大张慧”,我们都跟小张卉好,用小孩特有的刻意说起“大张慧”:小腿很粗,腰上都是肉,皮肤又黑又红,总像在农村刚刚割了谷子回来。夏天总穿一双红色的塑胶凉鞋,鞋袢都断了,用黑色鱼线歪歪扭扭地缝起来,像一个触目惊心的疤趴在脚背上。冬天永远穿一件藏蓝色棉祆,从来没有换下来过,袖口锃亮。上课一直举手,不举手也跟着老师大声说话,笑起来的咯咯声太大太刺耳,最后以及最重要的是,她永远考
第一名。
每次开家长会,卖毛线的女人总穿得很整齐,夏天是一条水蓝色真丝连衣裙,配白色皮凉鞋,冬天是土黄色呢子大衣,围大红色羊毛围巾,围巾平时都是张慧在戴,大概太多年没有洗过大红色变成稀脏暗红,又被咬出了几个小洞,围起来看不到脖子,显得她的头惊人的大。
她年年都顶着大头上台去介绍教育经验,台下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教室里有一种漫不经心却精心策划的冷漠,只有张慧涨红了脸,似平马上就要咯咯笑出声来。家长会完了,她和张慧拿着成绩单和排名表,兴高采烈地往校门外走,从后面看上去,像两个圆滚滚的酸菜坛子在慢慢挪动。我们跟着自己的父母垂头丧气地走在后面,避免与她们擦身而过。她的毛线生意一直不好,妈妈们不知道是故意还是巧合总是去隔壁推上买毛线,即使是一模一样的花色与价格,别人挑毛线,她就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大家都是认识的,彼此都觉得尴尬,她就低下头来,继续打手上的手套或者围巾。有年忽然流行用棉线编成松松软软的围巾,她连夜打了几十条挂在推子前,流苏留得很长,像香港连续剧里的女主角会戴的样子。围巾十块钱一条,她双眼熬得通红,人人都戴着上学,做作业时把流苏在手指上绕来绕去,只有张慧,还是戴着那条越来越暗的红色羊毛围巾,一到教室就摘下来,露出里面同样发黑的白色毛衣。
我和张慧都是近视眼,又都长得矮,永远坐在第一排,某次调整座位后,张慧坐在了我的旁边,她小心翼翼地把手到桌子的一角做作业,右手垂到了课桌下,下课又怯生生“你要不要吃柑子?”然后从书包里摸出一个小小青柑,剥皮一阵水雾升起,我们一人吃了一半,柑子没有熟透,让入难以忘怀的酸。她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家里有几个熟了的,很甜,你去我家吃好不好?”中午放学的时候她又说了一次:“你去我家吃柑子好不好?”
我们走过她妈妈的毛线摊,她很大声地说:“妈妈,我同学要去家里玩一会儿。”卖毛线的女人疑惑地看着我,却还是把钥匙递过来。张慧带着我从公共厕所后面的一条小黑巷子走过去,曲曲折折拐来拐去,走了许久许久,这才到了她家,推开门是个小院,满地青苔,洗澡盆里泡一堆衣服,有几朵粉红粉黄的月季开在边上,水龙头旁的青石板上放着三个漱口杯,牙刷的毛快掉光了,看不出哪一把是张慧的。我的牙刷和漱口杯是配好的一套,粉红色底色上有小白兔和彩色蘑菇。张慧踩在腻滑的青苔上,她好像微微闪了闪,却没有摔下去。
她兴奋地招呼我进去,又拉开了灯,小城里的所有人的家大概都差不多,是监狱般小小的铁窗和晃眼的白炽灯泡,仿皮沙发磨损得厉害,我们就坐在上面吃柑子,她挑来挑去,挑了个稍微有点发黄的,剥开一吃果然很甜,柑子皮被她细心地放在了窗台上。“我妈妈以后用来做菜,”张慧说,“陈皮兔很好吃,下次你也来吃。”又过了一会儿,她忽然从五斗柜里拿出瓶果珍,倒出开水给我冲了一杯,兴奋地问我:“好不好喝、好不好喝",果珍大概放得太久,结成了块,怎么都泡不开,又没自放够,喝起来只有一点淡淡的味,我随便喝了两口,就说:“我要回家了。”
张慧跟着我一起出去,她妈妈已经热好了剩饭剩菜,在毛线摊上等她。走了很远,我还闻到温热米饭和炒香了的豆瓣混杂海椒的味道,张慧毫无理由地咯咯笑起来,我回过头去看到她黑黑红红的脸,即使在正午金黄的阳光下,她也依然不是个好看的姑娘。
上高中那一年,电影院彻底关了,它変成了一个有无限可能的地方。有时候住进不知道哪里来的杂技团,铁笼里锁着狮子和老虎,就搁在门前的小广场上,公狮病病恹恹,一股骚臭忧郁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面前是一块发臭的生牛肉。有时候会扔一只已经半死的小公鸡进去,所有人都停下来,看它怎么艰难地把它撕成一块块,鸡血四溅,留下的印子很久都没有洗掉。小丑打扮妥当,坐在露天里吃红油抄手,喝汤的时候红色圆鼻头浸了进去,出来时上面流下一滴油。驯兽女郎们穿得极少,踩高跟鞋站在毛线摊前,商量着给男朋友打的毛衣选圆领还是鸡心领,又或者给自己钩一件今年流行的小披肩。卸掉重重浓妆,她们也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唇边还有细级绒毛,皮肤因为四处迁徒被晒得很黑,却依然透出光来,男友大都留在家乡,也有人跟团里的驯兽师好上了,隔着狮子和老虎眉来眼去,演出结束后偷倫在卡车车厢里做爱。
卖毛线的女人不会说普通话,和馴兽女郎们比划着讲价,彼此都憋得满脸通红,只有张慧放学后才能帮上忙。过了这么多年,她似平还是没有长高,又胖了一圈,下巴层层叠叠都是肉,堆在高领毛衣上,胸部又过度发有育,她戴上了很厚的跟镜偶尔做作业太累了摘下来,眼晴周围有一圈深印,轮廓模瞬我猛然觉得,这是一个陌生人。
她的成绩突然掉了下去,从第一名掉到了第十名上下,毫无缘由,她一直都是彻底扑在书上,在小城里,这种排名意味着考不上重点大学。大家掩盖不住“我早知道”的莫名欣喜在背后窃窃私语,说:“死读书的人都这样。”她于是更加死读起来,取下眼镜时有越来越明显的黑眼圈,一直黑红的皮肤开始透出蜡黄,嘴唇泛紫。我们都有点怕她,更加故意不跟她说话,下课凑在一起大声讨论昨晚的香港连续剧一一《妙手仁心)《鉴证实录》《刑事侦缉档案》。只有张慧,咬着嘴唇死死盯住面前的立体几何习题册,上面画满各种各样的辅助线。
卖毛线的女人还是来参加家长会,她火速老了、头发大概多年没有烫过,像掺进粉笔灰,身上所有的肉都在下垂,眼角和嘴边是深深的彼纹,穿一身花里胡哨的棉绸长裤,露膀子小衫,像直接从床上过来。她不再被叫上台去讲授教育经验,家长会一结東,她和张慧便很快消失了她回到毛线摊上做生意,张慧坐在边上背历史,两个人都有血红的眼睛。
我背书包从她们身边经过、忽然想到几年前那个有金色阳光的中年,很想再喝一杯淡而无味的果珍、或者剥开一个酸楚的青柑,但我什么都没有说,我走过她们、就像走过两个生人。曾经的电影院前劇刚住进了一个新的马戏团、一只巨大的火烈鸟忧伤地站在铁笼中,它一定是太孤独了。
四
高考放榜那天,卖毛线的女人忽然来敲我家商户。那是八月初的川南,潮湿闷热的日子没有尽头,她站在白花花的阳光下,双眼红肿,语无伦次地说:“张慧还差几分上重点线、你们能不能帮帮她找找人?”她说得那样真诚迫切,让我们不好意思指出当中荒谬,在完全不着边际的五分钟之后,她匁匆走了大概赶去敲下一个窗户,走了两步又回来,说:“能不能给我喝口水?"”我从冰箱里找到一瓶柠檬汽水,我在她咕噜噜灌时问
她:“张慧呢?”“在家里,”她说,然后眼晴里掉下泪来,“张慧脸都哭肿了。”
张慧后来上了一个普通本科,英语系、她自己去的重庆拖两个编织袋,卖毛线的女人依然在卖毛线、她很快接受了现实,又开始四处打听、做翻译到底净不挣钱?大家都告诉她“很挣钱呢!还可以出国,挣的都是美元!”她一边打毛线一说:“那到时候我就不摆了、等张慧要友结了婚,我就帮她带娃儿去。
第一个寒假同学会我看见张慧,怯生生地坐在卡拉OK的角落里,穿一件有点旧的白色羽绒服,洗得很干净,下面是条牛仔裤,紧紧裹住她丰满的大腿,更让人诧异的是、她穿了耳洞,戴一对银色圈耳环,耳环很大,衬得她脖子更短,这的确是一个陌生人。我坐过去跟她说话、先是闲聊,忽然我问道:“你是不是耍了朋友?”她脸一点点红起来、用比我更加陌生的羞涩语气说:“还没有呢。”过了一会儿又忍不住怕悄说:“我倒是认识了一个人,数学系的。”音乐突然响起来,男生们扯着嗓子在唱《光辉岁月》,我一直没有想起来间她、关于那个数学系男生的一切。只是有一次在街上吃凉面,我看到卖毛线的女人,大声地跟身边的人说:“等这两年过去、我就去把头发染了,你看,我头发都白完了。
又过了两年,张慧死了。她得了韩国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白血病、我陆陆续听到她的消息:化疗了、她化好、她了很多、她昏迷了、她病危了。但是除了托人送两百块钱、我一直没有去看她,仿佛如此就可以视面不见。我的校友录也是如此,大家上传着新男友的照片,新买的裙子,从没有人提到过张慧的名字,在不管哪首歌曲中,她都是那个刺耳的音符,我们自动过滤了她的顿率,以寻求稳如一的动人旋律。
张慧死之后三个月,卖毛线的女人也死了,她那花花绿绿的毛线就此消失,那一带在某次城市改造中成为一个街心花园。电影院是小城最后暗下来的一盏灯,现在它终于灭了。
语丝文艺| |